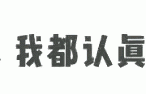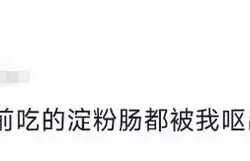文 | 彭彬
我与花椒,天生是有缘的。
去重庆上大学前,没听说过,“花椒”这个词儿;也不晓得,世上有这种麻味的东西;更不知道,还有人专门喜欢这种味道。上小学时,暑假捡蓖麻子卖,好奇用牙咬一口,又麻又涩,不好的味道。这是过往,唯一关于麻味的记忆。

大学食堂里,空气中都飘溢着麻辣分子,拼命往鼻子嘴巴里钻。菜肴品种,琳琅满目,几十大盆任你挑选,却清一色的麻辣。舌尖想独辟蹊径,享受无麻辣的味道,那是寻错了门。辣在老家很普遍,搭配上这儿的麻,似乎绝配,感觉辣的更香更醇更丰富了。主角是辣,配角是麻,倒是很习惯,并且很快就喜欢上了麻辣,重庆话“巴适得很”。有同学指点,菜里面,如喉症丸般大小的圆颗粒,褐色的,有一簇簇的附在小枝上,也有零星散落的,就是花椒,是它出的麻味。还说,从小就离不开它,语气带着自豪,很诧异我见识太少。
没几天,就想不起来,去寻不麻不辣的菜了。话又说回来,想去小饭馆,换不麻辣的口味,大师傅也不会做,满脸不可思议,“有毛病么!不麻辣,哪个做?”,“么”音还拖得老长,嘲讽得你怪兮兮的,低人一等似的,羞愧难当。唯一例外,就是油炸花生米,不放花椒辣椒;凉拌花生,也少不了麻辣调料呢。
北方来的同学,可没我等口福。他们本不吃辣,在加上花椒的麻,彻底溃败。刚来几天,常饿肚子的,满头大汗不说,还啧啧咂嘴,嘴巴成酒瓶状,不停倒吸着气,忙着往菜里加水,稀释麻辣,也难有成效。有的,不得不去小店,买方便面、饼干,配上榨菜充饥。
第一次尝到麻的厉害,是内江军训期间的一次晚餐上。报到一周后,新生们身着戎装,坐绿皮火车专列去内江站,再坐解放牌军用卡车去营地,浩浩荡荡的。重新分班,一班12名同学,教官兼班长。吃饭时,教官学生分开。一班一起吃,都是蹲着夹菜,站着吃。五个铝盆摆在地上,四个盛菜,一个盛主食,帮厨的同学提前摆好。主食,有时米饭,有时馒头。都大小伙子,长个子长力气的,米饭管够,小馒头带点甜味,很软很好吃,得抢才够数,我最多吃过六个。菜有荤有素,都是大锅菜分出来的,必须得抢,抢吃抢下手,大口嚼大口吞,动筷更要快。回锅肉是经典川菜,大片大片的五花肉,实在解馋,每次都最先被哄抢一空。吃得嘴巴油光可鉴,留下满口的麻辣余香。
闹过笑话。开饭时候,连长领着教官们开会,等他们回到食堂,馒头抢没了。师傅们只得再下面条,还挨了一次批,怪馒头蒸少了。第二天队列训练,班长好顿训话,骂动作不行,抢馒头倒行。师傅们憋着火,看出其中端倪,晚餐就换成我们倒霉了。回锅肉来了,一样的抢肉大战,一样的一扫而光。不一样的是,躺在盆里的花椒,却格外的多,肉眼判断得有四分之一盆。这时,满嘴满脑子麻木了,舌头也麻得失去了味觉。后面几盆菜,还是抢,习惯了,但没兴趣吃了,如同嚼腊,没滋没味的。夜里拉肚子,不停地跑厕所。四川同学,倒没受连累,肠胃早已百炼成钢、百毒不侵了。一旦花椒成了主角,辣椒退为配角,那种辣的“麻”,还真够人受的,我彻底服了。第二天轮到我帮厨,才晓得,是厨师们故意捣鼓的恶作剧,以解心头之恨。
返校后的周末,结伴化学系的老乡阿林,去逛解放碑,重庆最热闹的广场。中午瞧见小门头面馆,上面挂着黑底长条木牌,写着“老字号担担面”,字是金色的。对外就是一个大窗口,前面排了老长的队。我俩不约而同也跟着排,久仰“担担面”大名,就是冲着特色去的。在校园里,晚自习后,经常吃麻辣小面,六分钱一碗。我特爱吃其中的小油菜或海带丝。有同学吹牛说,真正好吃的,地道的,还是担担面。阿林在前面,点了碗普通的;轮到我,说要最正宗的。碗也不大,比装麻辣小面的大不了多少,也没油菜海带丝,就几筷子纯粹的面条,价格却高了不少,忘了是一毛五还是两角了。
阿林一米八的大个,嘴巴自然大点,几口就下去了,说麻辣得够呛,脸红扑扑的。我却摊上大事了,吃下一口,麻辣比那次回锅肉还猛,脸红淌汗事小,嘴巴突然没了知觉;再一口下去,耳朵从耳沿烧到耳根,红彤彤的、火辣辣的,又烫又疼,听觉也没了。老乡说的话,听不见,只见嘴巴一张一合。耳朵里不时冒出刺耳的长鸣,如同擦黑板时,金属与黑板摩擦发出来的。脑袋和嘴巴,包括舌头,都麻透了。担心舌头不听使唤,就使劲去说“听不见了”,幸好口型还有记忆。不错呢,老乡的嘴和表情还有回应,似乎是“不吃了算啦”,验明咱还没哑。眼泪汪汪的,也不知是麻辣闹的,还是源于没变成哑巴,心激动的。不管三七二十一,抓紧吃吧,面条囫囵着下去了,如同烫手的山芋在接力,抓紧转手,不脱手就起泡了。阿林的话不能听,也听不见,咱大义凛然,舍得一身剐,不剩一根面,银子不能白花呀。
过了近半个小时,才缓了过来。这担担面的调料,是一团紫红色的酱,正宗不正宗,取决于酱的多少。如此痛苦不堪,到底是麻狠,还是辣狠,或者各占一半,当时来不及分析。多年以后,遇到海南黄辣椒,与这次反应差不多。度娘说,四川辣椒在辣度上,比海南的差几个等级。这么说来,花椒成了催化剂,把辣椒催得更辣了。
寒假去高中同学,周三家做客。在随州东关街道上,半个四合院,院里铺着大块青石,有两棵石榴,还有葡萄架子。家境殷实得很,周叔好像是电力局的高官。那时周三还在复读高三,我俩曾经同桌一年多,他家对考上重点大学的我,自然高看几眼。满桌大席,是我那时遇到过的,最丰盛的大餐。
早馋开了,坐等周叔倒酒,大快朵颐。他突然想起,“你在重庆上学,肯定爱吃花椒吧!”,“没问题呀,随州哪有花椒?”。他说别人从四川捎过来的,泡在香油罐头瓶里。就让周三妈拿过来,放在我旁边,打开盖,放个小勺,让我尝尝。到现在我也不知所以然,想逞能,能抗麻呢,还是为了留住老家第一口花椒的味道,还是多天没吃麻味了,久旱逢甘霖?结果就是,不由分说,放进满满一勺嘴里。满桌人都惊呆了,直勾勾地望着我。我更得意,痛快咬了一口,妈呀,麻翻了,天快塌了!
周叔一脸关切,真心说,你太能吃麻了,我们都是舀一小勺,放碟子里,一粒一粒嚼,品味不下咽的。顺手倒杯白酒,我却尴尬住了,想吐出来,又不好意思,只得打掉牙和血吞。胡乱咬嚼几口,端起茶杯,生生把那要命的花椒,就着茶水吞了下去。即便如此,酒席的前半程,眼泪与汗,混在一起,忙着擦拭,掩饰着麻出来的“哭”。他们以为我胃口好,吃热了,一再劝我慢点吃。心里苦呀,却无处诉说,美味佳肴白瞎了,成了掩饰的道具,哪有心思品,品也白搭,满嘴里只有麻呀!
筵席过半,才渐渐忘掉麻味,美呀佳呀,味呀肴呀,终把魂钩了回来,细嚼慢咽、品滋享味。照旧酒醉饭饱,没辜负周家的一片好心,那勺花椒的遭罪,总算没有白受。
现在炒菜,辣椒不敢放,因为女儿怕辣。但花椒必须放的,山东的花椒,还嫌不够麻。从网上下单,专买重庆产的,才够味。
这辈子,算是离不开花椒了!

彭彬:山东济南人,祖籍湖北随州。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士,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历,高级国际商务师。在济南钢铁厂工作二十余年,后辞职下海,担任某物流公司高级顾问至今。业余爱好喝酒交友,读书写作,游山玩水,独处散步。2021年散文《车窗后的父亲》获得“诗意人生”华文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一等奖、《母亲的最后时光》获得“蒙东杯”首届“爱的盛宴”全国征文比赛一等奖。
壹点号山东金融文学
新闻线索报料通道: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,或搜索微信小程序“齐鲁壹点”,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!